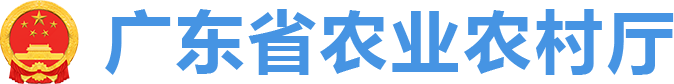农业部:我国农村改革试验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农村改革试验期限一般为3-5年,这样的期限之内也可以说在一个小范围内是可控的。取得成绩以后,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内进行适度的推广。
记者:第一,试验的期限有没有明确?第二,刚才张司长和宋主任都介绍到,我们从1987年开始搞了试验,这些多的试验有没有比较好成功地得到推广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张红宇:期限从方案设计的角度来看,一般各个地方的时间是三到五年,希望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一些大的成功经验。其实经过这个试验的过程,即便是出现问题也应该曝露了,这样的期限之内也可以说在一个小范围内是可控的。取得成绩以后,是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内进行适度的推广。
这个问题跟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是连在一块的,从80年代末搞的试验区来看,在一些大的方面,刚才宋主任讲到,我们在贵州湄潭搞的农村土地承包的试验,现在整个贵州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包括很多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些调整的问题,在贵州这个地方就是坚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方案就是从湄潭开始,进而向全国推广。再比如我们曾经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流通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在河南新乡的试验成果,对进入新世纪以后完全放开粮食购销的农产品改革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再比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苏州搞的相关试验改革内容,对推进城乡一体化,我在很多地方讲过,我们从全国层面来讲,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特别是十六大以后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南地区其实在一个范围内已经呈现一体化的实践,那时候要素流动还不是像现在可以全面流动,是一个区域范围内劳动力、资本,包括土地得到优化配置,对推动80年代和90年代那个地方的乡镇企业发展,进而对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苏南地区为什么走得这么好,跟我们80年代末设立了试验区或多或少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个推动对整个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对毗邻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容低估的。
宋洪远:首先关于周期的问题,我们在农村改革试验区运行管理办法里对试验方案的设计明确有一个要求,任何一个试验方案不仅要有布点安排的考虑,而且要有进度安排的考虑,进度安排就是比如这个主题有三个项目,三个项目可能这个项目具体需要三年完成,另一个项目具体是要五年完成,另一个项目需要七年完成,在方案里都要写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周期安排的事情,是由每一个具体的项目都有具体的时间安排,不可能永远试验下去。
第二,对于试验成果,我们有两种基本的态度和处理办法:一是成功的经验。成功的经验按照程序要推广,推广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为中央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参考和依据,很多试验的做法都写进了我们的政策和法规。比如刚才张司长举到的例子,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的试验,不仅写进1993年的文件,而且写进了土地承包法,是予以提倡的。还比如安徽太和搞的农村税费改革试验,当时的做法是“归费为税征收办法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搞了逐步取消农业税的试验。我们的税费改革就是这样,2000年到2003年全国做试验,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就是归费为税。还有新乡,当时对粮食流通的改革,试验是八个字“稳购、压销、保量、放价”。我们的粮食生产改革基本上按照这个路径走的,所以这些都是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被我们的政策和法规采纳了。还有的地方试验以后,发现这个走不通,如果不行,试验就完结,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成功定有成功的经验,失败定有失败的教训。我们说的是试验区,不是示范,如果成功了作为经验推广,失败了作为教训别人汲取。这也是一大功能。
包括我们这次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我们的思路和刚才宋主任讲的一样,跟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路没有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在可控的范围内,比如说金融改革试验,机构创新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在一个县设立新的金融机构,包括服务,包括抵押产品的创新,从范围来讲,我们没有希望搞得更大,有的地方提出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搞相关的试验,从风险可控的角度来讲一个县更为妥当一些,在机构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方面,经过三五年的改革试验,感觉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果有积极作用,范围适度扩大,这就是我们试验的目的。如果说我们在改革试验过程中遇到了偏差和问题,我们就及时地将相关的试验内容停止,这样风险就可控,跟上个世纪从路数上讲没有太大的差距,好的经验及时总结,不好的要及时处理。